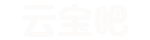语音变异(精选三篇)
语音变异(精选三篇)
语音变异 篇1
汉语方言已有研究表明,从方言与共同语(普通话)比较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方言词汇主要有三种类型(李如龙,2001)(1):
1)方言特有的词语,即方言固有词语(简称“固有词”)。如南京话的特有词:板牙(槽牙)、苞芦(玉米)、刀螂(螳螂)、拐角拉(角落)、泡汤(落空)、刷刮(快,利索)等(刘俐李等,2007:186~188)。
2)方言与普通话共有词语(简称“方普词”)。从共时视角来看,作为现代汉语地域变体的方言与作为现代汉语标准变体的普通话,两者之间理应存在大量的共有词语。事实亦如此,如《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中列有普通话词目(包括词和词组)1230条,笔者选择几个点作了统计,发现均有不低的相同率,如武汉话(属官话)达39.12%(481条相同),苏州话(属吴语)达31.22%(384条相同),长沙话(属湘语)达37.80%(465条相同),南昌话(属赣语)达43.50%(535条相同)。在方言与普通话共有词语中,既包括由古代汉语直接传承下来的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也包括不同时期从共同语借入并融入方言口语中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还包括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从普通话借入的词语(此类被划入第三种类型)。
3)从普通话转借过来的词语(简称“普入词”)。主要指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方言从普通话书面语中转借的词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方言词所没有的概念(如政治、时事、教育、科技等方面)而从普通话借入的,如上世纪50年代借入的“解放、土改、合作社、公社、丰产、大跃进”等新词语(李如龙,2001:105),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并迅速借入的,如“步行街、极品、内退、天价、房改、外教、BB机、DVD、IC卡、T恤、VCD”等新词语(陈章太,2002b:28);另一种是方言中已有固有的说法而借入的与方言固有词语并行并用的普通话的说法,如南京话的“梳子肉/扣肉、虎爪/鬓脚、平顶(头)/平头、火萤虫虫/萤火虫”等(刘丹青,1995:42~198)。
汉语方言中常有这样一种语音变读情况,某字在方言固有词语中读一种读音,而在普通话进入的词语(大多是原方言中没有的概念)中又读另一种近似普通话的读音。如南京话中的“今”在方言固有词语“今个(儿)、今年子”中读kn31,在普通话进入的词语“当今、如今、今非昔比”中则读tin31;“明”在方言固有词语“明儿(个)、明年子”中读mn24,在普通话进入的词语“明天、明年”中则读min24(刘丹青,1995:270、258~259)。又如福建泉州话中的“前、空、气”在方言固有词语“前次、空房、傻里傻气”中多读tsu珓i24、k‘a33、k‘ui21,在普通话进入的词语“前方、空间、生气”中则多读tsian24、k’33、k‘i21(2)(李如龙,2001:63)。方言学界将此类语音变读现象归之为文白分读(李如龙,2001:62;刘勋宁,2003:1;王福堂,2005:38)。笔者以为这种同一个字在不同类型的词语中读音不同的现象应属于语音变异现象,此现象的出现应该与词汇类型有关,即词的不同类型与语音变异可能存在着相关性。是否存在相关性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与科学论证,而方言学界未见有此方面的分析研究。
社会语言学有关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已关注到词汇系统与语言变异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如王士元、沈钟伟(1991)通过对上海市区/2/和/ɑ~/两个鼻化元音合并这一个案研究,发现词的使用频率与语音变异存在着相关性;徐通锵(1991)通过对现代宁波方言声调变异的调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两项研究均表明词的使用频率与语音变异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即词的使用频率对语音变异具有制约作用。而对于词汇类型与语音变异之间是否存有相关性问题,社会语言学界也缺乏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以江苏溧水“街上话”语音变异为例,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就词汇类型对语音变异是否存在着制约性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并对其原因作出初步解释。
二 语音变异的调查与词汇类型的确认
(一)调查情况的说明
溧水是南京市的一个郊县,县城为在城镇(近年改名“永阳镇”)。其方言在城话属于江淮方言,居民称之为“街上话”。为调查溧水街上话的语音变异情况,2004年4月,笔者编制了100组涉及语音变异的词语或习惯说法作为调查词表,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按1‰的比例(县城居民约5万多人)抽取50人作为当地不同街道、年龄、职业、性别居民的代表。要求每个被调查人必须是在县城长大,以街上话为日常用语。按年龄段分四个组:青少年组(10~20岁)、青年组(21~40岁)、中年组(41~50岁)、中老年组(51~65岁),每组调查10人,青少年组多调查10人。注意男女性别比。被调查人涉及当代中国社会十大社会阶层(陆学艺,2002:8~9)中的“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等六个阶层,我们将其中的“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合并为“经营管理人员阶层”,这样就涉及“经营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等四个社会阶层。
(二)词汇类型的确认
100组词语或习惯说法中包括含同一调查字的成对词语20组。其中“苋菜/马齿苋、挖土/用锹挖、嫁人/出嫁、心满意足/满意、俗气/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初中”等6组成对词语,依据前文方言词汇类型的划分,内部属于同一类型词语(即“方普词”),其他14组各自分属不同的词汇类型。鉴于本文着重探讨词汇的不同类型是否对语音变异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属于同一类型的6组成对词语不在本文研究之列,而分属不同类型的14组成对词语属于研究分析的重点。下面具体确认这14组成对词语中的28个词语(见表1)各自所属的词汇类型。
在“通济街地名/街上、庙巷地名/巷子、西坛新村地名/醋坛子、染脏布、衣服等沾染灰尘等时易显现出/传染”4组成对词语中,“通济街、庙巷、西坛新村”为溧水县城地名,属方言固有词,“染脏”为方言说法,也应属于方言固有词;而“街上、巷子、醋坛子、传染(3)”则既是普通话常见的词语也是街上话中常用的词语,应属于方言与普通话共有的词语,即“方普词”。这4组成对词语构成“固有词”与“方普词”两种词汇类型的对比。
在“发酸/酸菜鱼、换一件/替换、得罪/犯罪、牛角/角度”4组成对词语中,“发酸、换一件、得罪、牛角”属于方言与普通话共有的词语,即“方普词”;而“酸菜鱼、替换、犯罪、角度”属于街上话所没有的概念而从普通话进入的词语,即“普入词”。应该说有的进入的时间还并不长,属于新近进入的词语,如“酸菜鱼”(4)。这4组成对词语构成“方普词”与“普入词”两种词汇类型的对比。
“家去/回家、睏觉/睡觉、掼了一跤/摔了一跤、鳗鳝/鳗鱼、老鼠子/老鼠、绿佬/绿颜色”6组成对词语与其他8组成对词语不同,“家去、睏觉、掼了一跤、鳗鳝、老鼠子、绿佬”是街上话中的固有词语,而“回家、睡觉、摔了一跤、鳗鱼、老鼠、绿颜色”则“由于普通话的说法更具普遍性,方言区的人也接纳了共同语的说法”(李如龙,2001:105),属于同义词语并行并用。这6组成对词语构成“固有词”与“普入词”两种词汇类型的对比。
这样我们依据词语所属的词汇类型,将14组成对词语根据其词汇类型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对比组:“固有词/方普词”“方普词/普入词”“固有词/普入词”,具体见表1。
三 词汇类型与语音变异的相关性分析
(一)调查数据的统计
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指出,在语言变异中如果某一个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一抽象的语言形式就是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组成语言变项的语言变式(linguistic variant)(徐大明等,1997:100)。语言变式又可以分为:“旧式”(原有形式)、“新式”(新出现的形式)和“过渡式”(原有形式与新出现的形式之间的中间状态)等三种类型(郭骏,2008:133~141)。
拉波夫(Labov)曾指出,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新旧两种形式对立存在,新式最后要战胜旧式(Labov,1994/2007:66、300~301)。可见新式代表语言发展的方向,因此语音变异中的新式在不同词汇类型中的出现情况就成为我们研究词汇类型与语音变异的相关性之关键。依据调查材料,我们可统计出涉及多个语音变项中的不同新式在“固有词”“方普词”和“普入词”等不同类型词语中的出现数据,具体见表1。
依据表1,我们从对比组内部的新式比来看,新式在“固有词/方普词”“方普词/普入词”“固有词/普入词”三对比组中的分布不均衡,如“方普词/普入词”的新式比为18.8∶30.3,“固有词/普入词”对比组的新式比为7.5∶11.7;从新式在“固有词”“方普词”和“普入词”三种不同类型词语中所出现的平均数来看,新式在三种不同类型词语中的分布存在差异性,即固有词<方普词/普入词(13.5<18.9/19.1)。由此可见,新式在三类词语中的出现数已初步表明新式的分布状况与词汇类型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二)相关性的定量分析
鉴于语言变异研究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调查所得的大量资料只有通过定量分析才能说明问题(陈章太,2002a:110;游汝杰、邹嘉彦,2004:15)。在此我们采用专门分析变异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以有效地分析语音变异与词汇类型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此分析法是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研究中的一种标准化技术,其任务是分析特定变式与环境条件中哪些因素具有显著性的同现关系。变项规则分析法是将同一种因素在许多不同环境中的影响力综合起来考虑,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力被赋予一个确定的概率,称之为“作用值”(徐大明,1999:26)。作用值都介于0~1.00之间,如果介于0.50~1.00之间,则说明这个因素相对于因素组中的其他因素而言更有利于变式的出现(徐大明,2006:36)。
下面我们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对词汇类型与语音变异的相关性作定量分析,即对词汇类型与新式同现概率进行估算。采用的分析软件是Goldvarb2001。其中“固有词”“方普词”“普入词”三种词汇类型为自变量,新式的选用为因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显示:1)在三种词汇类型中,“普入词”和“方普词”这两种词汇类型的作用值介于0.50~1.00之间,表明词汇类型对新式的选用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证明词汇类型对语音变异具有制约作用。2)不同类型的词语在对新式选用的作用值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作用值呈递增模式:“固有词”的作用值为0.417(<0.50),不利于新式发音的选用;“普入词”“方普词”的作用值分别为0.536、0.560(>0.50)(5),有利于新式发音的选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词汇系统对语音变异的制约过程中,除了词的使用频率对语音变异存有制约作用外,词汇类型对语音变异也具有制约性,而且不同类型词汇对语音变异的制约存在差异性。
社会语言学定量分析的“定量模型原则”(principle of quantitative modeling)要求在研究语言变异时应关注变式出现时的语境特征(contextual feature),既要关注变式出现的语言环境,也要关注变式出现的社会现象(徐大明,2006:30)。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语言表现是由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的诸多因素共同确定的。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语音变异时,需要对新式选用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现象同时作定量分析。这样,既可检验在与社会因素作综合分析的情况下词汇类型是否仍显现出与语音变异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又可检验语音变异是否是语言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将“词汇类型”(“固有词”“普入词”“方普词”)和“社会因素”(“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同时作为自变量输入变项规则分析法的统计程序,统计结果显示,“词汇类型”成为有效地解释新式选用的环境变项,而“社会因素”中只有“年龄因素”为有效的解释因素,排除了“性别”“社会阶层”两个没有解释力的环境变项,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显示:1)“词汇类型”对新式发音选用的作用值,无论是单独分析还是与社会因素同时分析,其结果是一致的,再一次证明“词汇类型”对新式的选择存在相关性;2)“语言因素”(词汇类型)与“社会因素”(年龄)同时对新式发音的选用产生制约作用,再一次印证:语言变异是语言结构系统内部因素和语言结构系统外部的社会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语言内部某一因素单独制约的结果;3)年龄因素是制约语音变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青年、青少年采用新式率高,印证了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钱伯斯(Chambers,2002:349~372)曾提出的语言变式与年龄相关性的标准模型:新出现的某一变式在最年长一代人的话语中少量出现,在中间一代人的话语中有所增加,在最年轻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
(三)相关性的原因试释
已有研究表明,就街上话的整体而言,其演变方向是普通话而不是中心城市方言南京话(郭骏,2007:135~136)。就具体调查字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其旧式、新式(6)与普通话的接近情况来确认其演变方向:就旧式而言,声母相同6字,韵母均不同,调类相同12字;就新式而言,声母相同13字、相近1字,韵母相同6字、相近8字,调类全部相同。这就表明由旧式到新式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方向。正如陈章太(2002b:32)所指出的:“因为受普通话的强大影响,各地大小方言都发生较大的变异,总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
那么同时受普通话影响,同样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方向性,为何同一字在不同类型的词语中其新式的出现率会不同,为何“固有词”不利于新式的出现而“普入词”“方普词”有利于新式的出现呢?这是由不同类型词语所呈现的不同特性所决定的。现简要分析如下。
“固有词”为普通话无而方言特有的词语,为居民日常交际中的常用词语。溧水县城居民虽然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比街上话高,但街上话仍是居民的主体语言(郭骏,2007:140)(7)。这就意味着“固有词”有着很高的使用率,而高使用率有利于街上话原有读音的保持,这样受普通话语音的影响自然要小,所以新式的出现率就不高。据表1可见,固有词中的“家去、睏觉”没有出现新式,“通济街、庙巷、掼了一跤、鳗鳝、绿佬”等词新式的出现率都不高。只有属于地名词的“西坛新村”中“坛”较为特别,其新式的出现率极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名是方言变化的“见证人”,是语言的活化石,更易保留方言中的原有读音,这从“通济街”“庙巷”两个地名词新式的低出现率中可看出。为何“西坛新村”中“坛”的新式出现率极高?这可能与该地名出现的时间有关。“西坛新村”是一个居民新村,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建命名的,属于一个新地名,而“通济街”“庙巷”则是沿用了历史街名和历史巷名(参见《江苏省溧水县地名录》)。由此可见,原有地名其读音易采用旧式,新近命名的地名其读音易采用新式。
而“普入词”和“方普词”则不同。“普入词”是从普通话转借来的词语,由于方言中原本没有这样的词语,因此,在转借时自然极易受到普通话语音的影响。所以无论是方言中无固定说法而从普通话中借入的词语(如“酸菜鱼、替换、犯罪、角度”),还是方言虽有固定说法但因普通话说法更普遍从而借入的词语(如“回家、睡觉、摔了一跤、鳗鱼、老鼠、绿颜色”),这些词语在折合成方言语音时自然要比其他类型词语更容易受到普通话读音的影响,更易采用接近普通话读音的新式,即“把普通话的某类音值转换为母方言中的近似音”(张树铮,1995:96)。就“方普词”而言,“街上、巷子、醋坛子、发酸、换一件、得罪、牛角”等词语虽是街上话中的常用词语(也是溧水全县各乡镇方言中的常用词语),但同时也是普通话中的常用词语,因此在普通话的巨大影响下,在对普通话具有较高认同度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参见表3)更易采用接近普通话读音的新式。不过仍有个别词(如“街上、巷子”)新式的出现率不高,大多采用过渡式(见表1)。
四 结语
我们通过对溧水街上话中不同词汇类型对语音变异制约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词汇类型对语言变异具有制约作用,不同类型词汇对语音变异的制约存在差异性,“普入词”和“方普词”有利于新式发音的选用,“固有词”不利于新式发音的选用。这表明语音变异除受到词汇系统中词的使用频率制约外,也要受到词汇类型的制约,词汇类型也是词汇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我们通过对“语言因素”(词汇类型)与“社会因素”(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对语音变异制约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再一次证明词汇类型与语音变异存在相关性,同时也表明“语言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对新式发音的选用产生制约作用。
浅析赵本山小品语言的语音变异美 篇2
—10级中文系对外汉语韩文利
摘要
在修辞学领域,变异是在遵循语言规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语言创新的重要手段。变异修辞就是从变异的角度来探讨言语表达的修辞效果,是一种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变异修辞学正是从变异入手,探讨言语表达是怎样通过对规范的“突破”来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的。在小品语言中,因题旨情境的需要而进行的语言变异使其达到比规范用法更加有效的修辞效果。
关键词
赵本山小品语言
变异修辞
谐音变异
韵律变异
摹声变异
变异性修辞是相对于规范性修辞而言的。冯广艺的《变异修辞学》中指出,“语言规范和常规修辞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言语变异具有灵活性;语言规范和常规修辞具有规约性,言语变异具有创造性;语言规范和常规修辞具有全民性,言语变异具有独创性。”与普通修辞学相比,变异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单一集中,主要从声响形态变异、简单符号变异、聚合单位变异等方面对变异性修辞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它们的运行规律和修辞功能。其中,声响形态变异就是声音形式上的变异手段。从符号学观点看,它是利用声响形态因素的个别的临时的变异;从美学观点看,它是一种听觉感知的音响形象的变异。
小品是一种语言艺术,它通过多种变异修辞方法打破语言常规,产生幽默、机智、俏皮的效果,成为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小品语言的变异修辞主要利用语言系统内的各要素和言语交际中各种手段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而形成的。
赵本山小品是中国喜剧小品的代表,其特色化的语言使它在当今中国文艺舞台上独树一帜。赵本山小品语言通过多种变异修辞手法出人意料地将现有的语言材料改头换面、重新组装,使语言在瞬间闪现出耀眼的火花,从而使观众在反差中享受难以言传的快感。冯广艺在《变异修辞学》中提出了声响形态变异、简单符号变异、聚合单位变异等多种变异修辞现象,其中声响形态变异修辞手法更加突出鲜明地表现出赵本山小品语言的语音变异美。因此,本文分别从声响形态变异的谐音变异、韵律变异、摹声变异来探析赵本山小品语言的超常设置。
一、谐音变异
冯广艺在《变异修辞学》中指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同音异义、一音多义、一音一义、一音同义等构成了音义结合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也指出,谐音是构成幽默风趣的重要手段。谐音的巧妙运用,含义深刻,话语诙谐,可以增加语言的艺术情趣。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声响形态变异的谐音变异利用语言的音义结合特点,把音同或音近的不同语言单位巧妙地联系起来,构成各种表达方式,使小品极具幽默效果。
(一)同音异形的变异
音同异形的变异根据音义结合中同音异形的情形,通过谐音构成特殊的表达方式。冯广艺认为,这种同音异形的变异,利用了不同语素声音相同的特点,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表达效果。赵本山小品语言正是利用了同音异形的变异
手段,使其小品达到风趣的效果。例如:
1、赵本山
听你妈说你搁哪研究爹呢? 范伟
不是,没有,研究木乃伊。赵本山
哦,研究姨呢? 范伟
不是姨,是古尸。
赵本山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啊,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床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你要不勤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范伟
爸,这个“尸”是“尸体”的“尸”。
(小品《送水工》)
2、教练
等……等一下,等一下啊,先不急着换衣服,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基功。
队长
鸡公,带来没?
教练
基功不是带来的,基功就是基本功,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
仿生学的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队长
猫在散步。
(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例1中的“尸”和“诗”同音异形,谐“古尸”构成“古诗”,赵本山采用了同音异形字的变异手段,利用了不同语素声音相同的特点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表达效果,增加了小品语言的幽默效果;例2中的“基功”和“鸡公”同音异形,赵本山利用不同语素声音相同的特点,采用这种同音异形的谐音变异手段问基功“带来没?”,基功是人自身的基本功,自然没有带来不带来的说法,这样就使小品极具喜剧色彩。
(二)同音同形的变异
同音同形的变异是利用声音相同,形体也相同的语素(或词)构成的。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指出,同形异义现象是相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笑话、逗乐、插科打诨以及字谜、灯谜等文字游戏不可缺少的材料,巧妙运用它可以增加语言的情趣。赵本山小品语言正是利用了同音同形的变异手段表达其具有幽默趣味的思想内容。例如:
1、宋丹丹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赵本山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呀?那么多年了。宋丹丹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赵本山
电网呀? 宋丹丹
嗯。
赵本山
电脑的上网? 宋丹丹
电脑网。赵本山
啥网呀?
宋丹丹
因特儿网呀!
(小品《钟点工》)
2、赵本山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 范伟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赵本山
错!
高秀敏
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来。赵本山
正确!
范伟
你出生的那个生啊……
(小品《卖车》)例1中,“上网”的“网”与“鱼网”的“网”同音同形不同义,此处由表示“无线网”的“网”谐出“鱼网”的“网”,这种言语表达跳跃性大,出乎意料,引人入胜,增强了小品语言的趣味性;例2中由“生长”的“生”谐出“出生”的“生”,“生”在这两种情况下同音同形而含义不同,赵本山巧妙地运用同音同形而含义不同的语素,利用这种同音同形的谐音变异手段表达别有趣味的另外一种语义内容,造成巧移语义、衔接自然的表达特点,使观众开怀大笑。
(三)音近形异的变异
音近形异的变异是表达者有意创造一种与原有的语素或词音近形异的言语单位来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指出,有时利用谐音的方式,故意寻找字面上可以望文生义的特殊的汉字,使字面意思同原词语的意思毫不相干,能把外来词语变成游戏、逗乐的手段。这种变异手段使赵本山小品语言引人入胜,幽默风趣。例如:
1、赵本山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宋丹丹 你不明白你问啊!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激死特(psychologist),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小品《钟点工》)
2、孙立荣
感谢铁岭气象台 赵本山
电视台
孙立荣
感谢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赵本山
栏目组
(小品《捐助》)例1中的“赛考类激死特”与“psychologist”音近形异,它表现了小品中人物对现代生活的不了解,更进一步突出了主题思想,宋丹丹在小品中利用中文与英文的谐音构成音近形异的变异修辞手法,增添了小品的趣味性;例2中“拦不住”与“栏目组”音近形异,表现出小品中人物的紧张心理状态,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赵本山利用方言的不同发音构成音近形异的变异修辞现象,造成一种特殊的言语气氛,具有较强的表达作用,让观众大跌眼镜。
(四)谐音别解的变异
谐音别解的变异就是用与原语言单位谐音的手段,对其作出与原义迥然不同的解释。赵本山小品语言正是利用了这种谐音别解的变异手段,用与原语言单位同音异形的词语,作出与原义不同的解释,从而达到出乎意料的诙谐效果。例如:
1、崔永元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赵本山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小品《说事儿》)
2、宋丹丹
秋波是啥玩意,你咋都不懂呢,这么没文化呢。赵本山
啥呀?
宋丹丹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小品《今天 昨天 明天》)例1中用与“专机”谐音的手段将“专机”谐音别解为“拉砖拖拉机”,例2中用与“秋波”谐音的手段将“秋波”谐音别解为“秋天的菠菜”,赵本山小品语言正是通过对原有语素、词或短语的谐音并扩展进行别解,用与原语言单位
谐音的手段,作出与原义迥然不同的解释,使言语表达富有变异特征,形成谐音别解的变异现象,让观众捧腹大笑,别有一番风味。
(五)谐音拈连的变异
在小品语言中,谐音拈连的变异主要依靠不同语素的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特点进行巧妙的拈连,表达出特殊的主义内容。例如:
1、赵本山
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话
疗”。
范伟
恩,还得化„„
高秀敏
老头子,哎,老头子。
赵本山
这病我可不看了,这啥玩意啊?大妹子,我这还没看呢,你别整
这事儿啊。
高秀敏
你咋的了,你?
范伟
媳妇儿啊,完啦!大夫都通知我化疗啦!
(小品《心病》)
2、赵本山
听你妈说你搁哪研究爹呢? 范伟
不是,没有,研究木乃伊。赵本山
哦,研究姨呢? 范伟
不是姨,是古尸。
赵本山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啊,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床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你要不勤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范伟
爸,这个“尸”是“尸体”的“尸”。
(小品《送水工》)例1由“话疗”的“话”谐音拈连为“化疗”的“化”;例2 由“古尸”的“尸”谐音拈连为“古诗”的“诗”,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谐音拈连变异以谐音为基础,通过谐音而拈连,从而有效地发挥其诙谐效果。这种谐音变异既有同音同形的现象,也有同音异形的现象,在这里例1中的“话疗”和例2中的“古尸”谐音拈连现象都属于同音异形的谐音拈连现象。
(六)谐音仿拟的变异
在小品语言中,谐音仿拟的变异主要通过谐音来进行仿拟,仿拟后的单位和仿拟前的单位具有音同或音近的特征,从而使小品语言更加幽默风趣。例如:
1、崔永元
剪彩时的情况呢?
宋丹丹
相当热闹,锣鼓喧天,红旗飘飘,人山人海。
赵本山
跑到养鸡场剪彩,剪完了就得禽流感了。死了一万只鸡,人家送她一个外号叫“一剪没”。
(小品《说事儿》)
2、崔永元
挖社会主义墙角!
宋丹丹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蚝社会主义羊毛。
(小品《今天 昨天 明天》)例1中“没”和“梅”音同,“一剪没”是“一剪梅”的仿拟;例2中“毛”和“角”音近,“蚝社会主义羊毛”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仿拟。这种类型的仿拟较一般的仿拟有不同的特征,它以音同或音近为基础,例1中的“没”和“梅”属于以音同为基础的谐音仿拟,例2中的“毛”和“角”则属于以音近为基础的谐音仿拟。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正是以音同或音近为基础构成谐音仿拟的变异,从而使其语言更加幽默顽皮,引人入胜。
(七)谐音双关的变异
小品语言的谐音双关的变异是利用谐音构成的双关形成变异性的言语表达,以此来增加它的幽默效果,看似此意,其实别有它意。例如:
1、赵本山
咱们是亲戚,我的姥爷住在大连。毕福剑
叫什么名字? 毛毛
毕门庭
毕福剑
你姥爷打麻将很厉害?
(小品《不差钱》)
2、毕福剑
你叫什么名字?
小沈阳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小沈阳。毕福剑
还有外国名字?
小沈阳
我英文名字叫“xiaoshenyang”
赵本山
英文名字叫小损样。
(小品《不差钱》)例1 中丫蛋说自己的老爷叫“毕门庭,而毕福剑却听成了打麻将的专业术语“闭门听”,“毕门庭”与“ 闭门听”谐音,构成语音双关,例2 中“xiaoshenyang”与“小损样儿”利用拼音与汉字的谐音,构成谐音双关的变异,表面说他的名字,实际是嘲讽他,如此表里相应含蓄而又不失幽默,让人捧腹大笑。
二、韵律变异
声响形态变异的韵律变异是一种利用语言的声响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变异方式。在小品语言中有时要求注意用韵的和谐完美,人们不得不为了韵律上的某种需要在言语表达上作一些异乎平常的调整,或者在韵律上作一些变换,从而形成别异的表达,使其极富诙谐幽默的效果。
(一)语言单位的结构调整
在小品语言中,言语表达者为了使语言表达符合韵律需要,常常采取变异手法,调整结构就是其中一种。
例如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赵本山的台词: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起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 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这段独白中“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就是为了押韵的需要而调整结构,将“更是天下难找”放在后面,而将宾语“人民军队”放在前面,从而使整个句段句式工整,韵脚和谐,节奏鲜明,让观众在简洁的言语形式中体会深意,同时又达到风趣幽默的艺术效果。
(二)语言单位的省略和添加
在小品语言中,为韵律和表达效果的需要可对语言单位进行结构上的省略和添加,这也是一种韵律变异手段。
例如小品《功夫》中赵本山的一段台词:
“那次卖拐把他忽悠瘸了那次卖车把他忽悠捏今天在十分钟之内,我要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跟你们俩当教师爷了。”
这段台词中“教师”是一个专用的固定名词,为了韵律的和谐工整和语义的表达,后面添加了“爷”这个语言单位而成为“教师爷”,这不仅符合了韵律 的需要,同时幽默之趣显明。
有时,为了节奏的匀称和韵律的需要,还采取一些“简缩“方法,例如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宋丹丹的台词: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哒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 这段独白中“美英合伙欺负人”就是因为韵律的需要,而将“美国英国”简缩为“美英”,一方面突出表现了其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使语言富有变异美。这不仅使节奏变得比较匀称,同时也增加了小品语言的诙谐效果
(三)语言单位的重复
小品语言中言语表达者在运用语言表演时,往往为了韵律的需要,重复某个语素词或短语,这也是一种韵律变异手段。
例如小品《钟点工》中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对白: 赵本山
嘿,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宋丹丹
怎么地?
赵本山
咱得弄明白我儿子叫你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宋丹丹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赵本山
三陪呀。宋丹丹
说啥呢?
这段对白中为了韵律的需要而将“说话”重复为“说说话”,将“聊天”重复为“聊聊天”将“唠嗑”重复为“唠唠嗑”,这样使整个句式工整流畅、朗朗上口。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为了韵律的需要而重复某个语素词或短语,形成韵律变异现象,同时也让观众忍俊不禁。
三、摹声变异
声响形态变异的摹声变异是摹仿某种声响形态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造成一种修辞效果。小品语言往往利用摹声变异,摹拟各种声音,使语言表达更具有动态感,从而充分发挥其幽默诙谐的效果。
(一)直接摹声变异
小品语言的直接摹声变异是指通过直接摹拟人或事物的声音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形成一定的修辞特色。例如:
1、高秀敏
前两天,他买彩票中奖了,中了三千块钱。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院,差点没过去。
赵本山
哎呀呀呀呀„„
(小品《心病》)
2、赵本山
我是有个问题想直接咨询您老一下
范伟
恩,你说
赵本山
我家有一头老母猪啊,黑地白花的啊,早晨一起来打开家门,以每小时八十脉的速度向前疯跑,“咣当”撞树上,死了!
(小品《功夫》)例1中“嘎”直接摹拟动物的叫声,充分表达出人物在得知自己中奖后难以承受的心情;例2 中“咣当”直接摹拟物体碰撞声,把猪撞到树上的情景描绘得活灵活现,摹声变异修辞效果突出,同时也让观众融入到小品中人物的表演情景中。
(二)间接摹声变异
间接摹声变异不是指直接摹拟其他声响,而是指通过某种人为想象的声
响和间接摹拟的声响而形成的言语变异手段。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也常常运用这一变异手段,例如:
1、赵本山
哎呀呀呀呀,我这还叭叭给人上课呢,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事呀?大妹子,大哥呀,不是,我这心呐哇凉哇凉的啊!大妹子,我这人啊,不是那种看不开事的,对钱这事无所谓。但对感情,我们两口子,就像我们两口子过的,你抽过去了,是吧?
范伟
我„„我抽了,我„„我都吐沫了。
(小品《心病》)
2、赵本山
别打岔,整没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来匆匆去匆匆,“唰“说没就没啊!
范伟
嘎„„
(小品《心病》)例1 中“叭叭”在这里指代人说话的声音,和人说话这一具体活动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属于间接摹声变异现象;例2 中“唰”这种摹声词摹拟了不具备某种声响的事物的声音,在这里指人生时光短促,属于间接摹声变异。在赵本山小品语言中,常常充分利用某种人为想象的声响和间接摹拟的声响形成一种言语变异,即间接摹声变异,以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引人入胜。
结束语
赵本山小品从带有唱腔的“二人转“语言到脱离唱腔走向舞台,它以各种语言手段构成戏剧语言,综合运用多种修辞变异手法,不断变换表现手法,增加了小品语言的表现力,提高了小品的可观赏性,它以诙谐幽默,讽刺滑稽的特点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打动了亿万观众,其言语表达技巧日臻成熟,堪称东北派小品的典型代表,成为春晚上最亮丽的风景,也为丰富艺术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语音变异 篇3
关键词:高变异语音训练法 发音人变量 声调习得 无声调语言
引言
汉语是有声调语言,通过音高变化来区别意义。对于绝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尤其是对母语为无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而言,声调是汉语语音习得的一个难点,即使是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声调感知和产出上仍存在问题。虽然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一再强调声调教学的重要性,但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帮助汉语学习者提高对汉语声调区别特征范畴化的知觉能力以及利用关键性声学特征感知汉语声调范畴间的差异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采用实验室训练的方法去提高二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语音感知能力,这种训练方法也被称为知觉训练法(perceptual training)。第二语言语音知觉训练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学者们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已经证明,知觉训练不但能够有效地提高二语学习者感知目的语语音的能力,而且训练结果能够维持得更加持久,能够迁移到新的语料、新的发音人甚至可以迁移到产出。(Logan et al,1991;Lively,1993,1994;Flege,1995b ;Bradlow et al,1997,1999;Wang et al,2003;Iverson et al,2005)
其中高变异语音训练法是运用最为广泛、效果最为明显的一种主要的知觉训练方法。这种训练方法最早是由Logan et al(1991)提出来的,这种训练方法强调构成训练材料的实验刺激的高度变异性(high variability),包括不同语音环境、不同发音人的声音等。相关研究表明高度变异材料(多名发音人和不同的语音环境)有助于学习者意识到范畴间差异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二语学习者感知目的语中新的语音范畴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迁移到新的刺激和新的发音人。(Lively,1994;Wang,1999)
但当前关于高变异语音训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此方法对提高二语学习者新语音感知能力的作用,而针对超音段音位(如声调)的研究还并不充分,对于构成高变异语音训练的各相关因素的功能及相互作用的研究还不完善。本研究希望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考察知觉训练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感知的作用。实验既从整体考察高变异语音训练方法对提高二语学习者声调感知的作用,也从构成不同训练方法的因素着眼,考察不同的训练材料对声调感知的影响,试图寻找到针对提高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感知能力的有效训练方法。
二、研究方法
(一)实验目的
本实验研究知觉训练的学习材料中发音人变异性对“零起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范畴感知的影响。重点考察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学习的两种知觉训练方法:使用“相同发音人”朗读训练材料的知觉训练法和使用“不同发音人”朗读训练材料的知觉训练法(即高变异语音训练法)对零起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范畴感知的影响以及不同的知觉训练方法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感知能力迁移到新的发音人的影响。
(二)实验方法
1.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2×3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采用前测-训练-后测-迁移测试的实验过程。
自变量:
自变量一是学习材料,是被试间变量,分“相同发音人”“不同发音人”两个水平。
自变量二是测试类型,是被试内变量,分成前测、后测和迁移测试三个水平。
因变量是辨别测试的正确率。
2.被试
被试为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水平为“零起点”的初级班留学生,没有其他有声调语言学习经历,未接受过长期的声乐训练。被试分成“相同发音人”“不同发音人”两组,每组10人,接受一种训练材料的训练。被试男女各半,年龄均在18至35岁左右。
3.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分成训练音节表和测试音节表以及迁移测试音节表。全部采用自然的单音节形式。共包括280个不同的单音节。前测和后测音节表是一个随机音节表,包括相同的80个单音节,只是呈现顺序不同。迁移测试音节表由80个与前测、后测及训练材料都不同的单音节组成。迁移测试音节表由四名新发音人(两男两女)朗读。音节之间的时间间隔(inter-trial-interval)为5000ms。
训练音节表的音节选择为自然音节,词的选取覆盖了不同的辅音和元音,以及单元音、双元音和多元音的结构(元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鼻音)。不同音节环境训练音节表包括120个不同音节,每类声调30个音节。
发音人是八名普通话水平为一乙的中国人(四男四女)。四位(两男两女)朗读迁移测试的材料,另外四位(两男两女)朗读训练材料(包括相同音节和不同音节的音节表),其中一名女性同时也朗读前、后测材料。“相同发音人”的训练材料是一个发音人朗读的120个声调不同音节不同的刺激,重复4次,构成480个刺激。“不同发音人+不同音节环境”的训练材料是四个发音人阅读的120个声调不同音节不同的刺激,构成480个刺激。四类声调两两为一组进行训练,共分六组(1-2;1-3;1-4;2-3;2-4;3-4),每组80个刺激,其中每类声调为40个。endprint
要求8位发音人以正常语速朗读训练音节表和测试音节表,并用Praat语音软件进行录音,语音样本都为16位单声道的录音,语音采样率为44100HZ。再利用Praat语音软件对声音文件进行编辑。在实验开始前,由2名汉语母语者对实验材料中所有音节进行辨别测试,准确率都应达到100%。
4.实验过程
测试阶段使用辨别测试,在电脑上利用E-prime软件进行测试。被试对听到的80个刺激(每类声调各20个,随机排列)进行辨别,判断是四声中的哪一个,并按下相应的数字键(“1”“2”“3”“4”)。每个刺激播放前,电脑屏幕中间会出现一个红色“+”符号注视点,提醒被试实验开始。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inter-trial-interval)为5000ms秒。被试要在5000ms内判断出所听到刺激的声调类别,并按下相应的数字键。测试过程中不提供反馈。正确的判断记一分,错误或漏选不记分,最后计算各组被试前测、后测和迁移测试的得分。
前测结束后,被试开始为期一周的三次知觉训练,每次训练时间为40分钟,前测与第一次训练为同一天,最后一次训练结束后开始进行后测,最后进行迁移测试。所有的训练任务均在电脑上完成,训练材料通过E-prime程序呈现。六组实验材料(1-2;1-3;1-4;2-3;2-4;3-4)按顺序依次训练,每组材料训练开始前,测试者告知被试该组训练的声调类别,每组材料训练结束后,被试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休息结束后被试按任意键继续下一组训练材料。在正式实验之前,所有被试均有10个项目的练习和讲解,目的是使他们熟悉实验要求。被试每次听到一个单独的刺激,需要辨别出听到的语音是两项给定选择中的哪一个(例如:一声还是二声),屏幕左下角和右下角会分别呈现代表声调调类的“1”和“2”,被试需按相应的“F”和“J”键。辨别正确与否会得到即时反馈,如果被试判断错误,屏幕将会呈现“INCORRECT!”,并重复播放上一个音节,被试必须按正确的键才能播放下一个音节,如果判断正确,屏幕将会呈现“CORRECT!”,但被试仍需重复按一次正确的键才能播放下一个音节,以避免无意的误按和连按。
(三)数据统计方法
被试完成前测和后测后,E-prime上会自动生成其测试结果,正确的记为1分,错误或未及时判断记为0分。将每组10名被试测试的结果得分进行平均,得出平均分,即为知觉训练实验的成绩。
(四)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对两组被试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其结果如下:
表1.两种知觉训练任务的前测后测及迁移测试成绩
前测 后测 迁移测试
单发音人 55.5 69.6 61.1
多发音人 54.3 69.0 67.9
我们进一步运用SPSS17.0对接受不同知觉训练材料训练的被试所做判断的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为:
(1)知觉训练材料主效应不显著(F(1,18)=.452,p=.510),说明不同的知觉训练(采用单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与采用多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对于汉语声调习得的效果没有明显差异。
(2)测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2,36)=54.283,p=.000),说明知觉训练方法能够显著提高被试汉语声调判断正确率。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前测和后测正确率的差异显著(p=.000),前测和迁移测试正确率的差异显著(p=.000),后测和迁移测试正确率的差异不显著(p=.061)。这说明使用两种训练材料的知觉训练都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汉语声调学习产生了学习效应,提高了无声调语言学习者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均可有效迁移到新的发音人和新的发音材料。
(3)知觉训练材料和测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36)=9.698,p=.006),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前测”水平上,“单发音人”和“多发音人”训练材料主效应不显著(F(1 ,18)=.22,p=.647),在“后测”水平上,“单发音人”和“多发音人”训练材料主效应不显著(F(1,18)=.86,p=.367),在“迁移测试”水平上,“单发音人”和“多发音人”训练材料主效应显著(F(1,18)=5.52,p=.030)。
图1.两种知觉训练材料前后测及迁移测试成绩的比较
(五)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两种知觉训练都能对无声调语言母语者的汉语声调学习产生学习效应,有效地提高了学习者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
此外,采用多发音人训练材料的知觉训练能有效使发音人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迁移到新的发音人和新的语音材料中,这也与前人的实验结果较为一致。(Wang,1999,Logan,1991)至于使用单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是否能够有效提高被试的范畴感知能力,不同实验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虽然本实验中使用单发音人组能够提高被试的声调感知能力,但是迁移测试结果表明采用多发音人语音材料训练的迁移效果要更好,这说明采用不同发音人训练材料的训练方法更有助于声调感知能力迁移到新的刺激和新的发音人。
Lively et al(1993)指出学习者语音的发展往往高度依赖于来自语音信息中提供的语音环境表征。关于回忆和记忆再认的研究也表明学习者的记忆中保留了基于特定发音人的语音细节。也就是说发音人的声音信息并未被学习者的选择记忆过滤或遗失掉,而是被整体地存储在记忆的合成表征中。所以当学习者接受了多发音人的训练材料,他们就会将大量的样例存储在记忆中,这些样例有助于他们形成抽象的稳定的原型,形成语音范畴,而单发音人的语音材料只能提供很少的范例,所以仅接受这种训练材料的训练,被试的声调感知能力有可能无法迁移到新的测试材料(不同的发音人、音节环境)中去。此外,Magnuson的研究中,他对比了5组使用不同单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进行知觉训练的被试,虽然前后测差异显著,但是其中有两组被试既没有产生学习效应,同时也无法迁移到新的发音人。Lively et al(1993)的实验也证明,即使是母语者,不同的发音人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的显著差异。endprint
在本实验中,采用多发音人和单发音人朗读的两种训练材料都能有效地提高学习者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但本实验训练材料的单发音人组只有一组,实验已经证明该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能够有效地提高被试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有效迁移到新发音人,但是在单发音人组如果使用其他发音人进行声调知觉训练,是否仍会产生学习效应和迁移效应,尚无法判断。此外,多发音人组的迁移测试成绩显著高于单发音人组,说明不同训练材料(单发音人和多发音人)对学习者的声调感知能力的迁移作用的差异显著,采用多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更有助于将声调感知能力迁移到新的语音材料。
三、对汉语声调教学的意义
第一,高度变异的知觉训练法为有效提高“零起点”无声调语音母语者汉语声调范畴感知能力提供了帮助。教师可在语音教室中采用知觉训练法对学习者进行声调训练。这种方法也可作为语音教学的辅助工具推广到网络教学中去,能够有效缓解课堂教学的负担。
第二,在知觉训练中,最好采用多发音人朗读的训练材料。采用这种训练材料并结合恰当的训练方法对学习者进行训练,不但能够有效而稳定地提高学习者的声调范畴感知能力,更有助于学习者的声调感知能力迁移到新的刺激。此外在避免单调的同时也能提供更多的语音信息,防止了单发音人个体差异所可能导致的诸多潜在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林军.知觉训练在第二语言语音习得中的作用——兼论对外汉语的语音习得和教学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 ,(1).
[2]Bradlow,A.R.,Pisoni,D.B.,Yamada,R.A.,and Tohkura.Training Japanese listeners to identify English /r/ and /l/IV:Some effects of perceptual learning on speech production[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97,(101).
[3]Bradlow,A.R.,Yamada,R.A.,Pisoni,D.B.,& Tohkura,Y.Training Japanese listeners to identify English /r/ and /l/:Long-term retention of learning in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J].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1999,(61).
[4]Flege,J.E.Second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Theory, findings,and problems. 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M]. Baltimore,MD:York Press.1995,(pp.229-273)
[5]Iverson,P.,Hazan,V.,and Bannister,K.Phonetic training with acoustic cue manipulations:A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teaching English /l/-/r/ to Japanese adults [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2005, (118).
[6]Lively,S.E.,Logan,J.S.,and Pisoni,D.B.,Training Japanese listeners to indentify English /r/ and /l/.II. The role of phonetic environment and talker variability in learning new perceptual categories[J].Journal of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1993,(94).
[7]Lively,S.E.,Pisoni,D.B.,Yamada,R.A.,Tohkura,Y.,and Yamada,T.Training Japanese listeners to identify English /r/ and /l/.III.Long–term retention of new phonetic categories[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94,(96).
[8]Logan,J.S.,Lively,S.E.,and Pisoni,D.B.Training Japanese listeners to identify English /r/ and /l/:A first report[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91,(89).
[9]Wang,Y.,Spence,M.M.,Jongman,A.,and Sereno,J.A. Training American listeners to perceive Mandarin tones. [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99,(106).
[10]Wang,Y.,Jongman,A.,and Sereno,J.A.Acoustic and perceptual evaluation of Mandarin tone productions before and after perceptual training[J].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20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