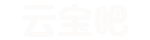创作阶段(精选四篇)
创作阶段(精选四篇)
创作阶段 篇1
面对历史和当下的陶瓷艺术发展现状, 回顾本人十年的陶瓷创作经验, 发现自身对个人意识的处理与实验性的创作一直贯穿在我的创作之中。本文也是希望通过对自我创作的总结与归纳, 寻找到个人陶艺创作的语言与规律, 并以此探讨未来创作的可能性。
总的来讲, 我的创作思路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器皿去功能化, 追求形式语言的偶发性。其作品以手工成型为主, 追求与自然协作。代表作品《皮囊壶》系列等。
第二阶段, 从对历史文本的热衷, 如魏晋书法和明式家具的审美体验, 到人与自我生活空间之间的关注, 在矛盾中追求和谐。代表作品《瓷书》系列等。
第三阶段, 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拓展, 回归到“物”的本质, 将个人体悟提炼并强调作品体现的观念性。手法上开始试验泥土的“可复印性”。代表作品《自述》《以死印生》等。
文中所指的“物”大体上可归纳为“自然之物”“历史文本之物”“艺术思维之物”暗合我创作中体现的偶发性、和谐性与观念性之特性。
一
《皮囊壶1》系列如图一, 创作于2010年, 这是我就读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时期的早期作品。在这件作品中, “壶“的功能被关注到最小, 其形态也被置换成纯粹的雕塑语言。当创作这件“物” (“自然之物”) 时, 可以说我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最优质的陶瓷材料训练, 这个阶段我非常关注泥巴本身形式语言的产生的多种可能性, 利用黑陶“致柔致硬”的特性, 有意将偶发状态下产生的质感与记忆一一保留:泥土在湿润状态下柔软且极赋可塑性, 而撕裂之后类似疤痕的质感又不禁让人联想起人类身体被伤害后的记忆, 但这种记忆的被唤醒是潜在的, 更多的是泥巴本身带来的, 而非意识的充分发挥。
同系列的《皮囊壶2》如图二, 在空间形态的处理上, 从积蓄膨胀的外形转化为内敛的收缩状态, 我利用钢筋将其架空、悬挂, 这改变了传统壶的放置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件作品与其最初的形态来源——“蒙古皮囊壶”驰骋沙场的气质更为吻合, 某种程度也赋予了这个器物一定的动物性与原始性。
在这个系列中, 泥土的偶发效果是我刻意表现的, 在看似宛若天成的自然肌理背后其实是我对泥性的有意经营。这个阶段, 我和泥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一方面放任泥土在造型过程中产生的自然质感, 另一方面又紧紧控制这种质感的限度与范围。在这个系列里, 泥巴是自然、柔软的, 而我的情绪与意识呈现的是一种含蓄, 内缩的状态, 这种状态更多的是泥巴直接带给我的感受, 我的意识其实是伴随泥巴的周折而周折的。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创作是材料先制作, 意识后产生的过程。泥土的偶发是顺和自然的发展而展开的, 是呈现泥土自然属性的最好的体现。
而我这阶段的作品似乎更符合和自然合作的概念, 这里的“物”是比较单纯的“自然植物”
二
《瓷书》系列如图三作品是我对“物” (“历史文本之物”) 的语言的另一种尝试。这是对魏晋书法用笔和明式家具的审美有感而作。在气度上, 我试图寻找书法的运笔走势, 而在细节的推敲上, 又将在明式家具上所感受到的雅致审美、高格调体验移植入作品之中。
《瓷书》系列作品是我将瓷与木的结合首次尝试。瓷与木结合在材料上是一种冒险, 这是硬与软的冲撞, 冷与暖的交织。但我试图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 “保护与抗争”“承载与依附”的悖论情绪一直伴随我创作到最后。
对矛盾的事物进行联系, 我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之前就十分感兴趣。中国古典美学里提到, 对常规事物的“反常”理解 (即称之为“反常合道”) 在表面上是对现事物的扭曲, 但却能形成艺术中的新奇效果, 但“反常”又必须“合道”, 虽意表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即生活常理合乎艺术之道。此处的矛盾最后都将化为和谐之力量。
因为有矛盾因素的存在, 所以在手法和视觉上我尽可能处理的单纯, 和谐:铜红釉和米黄色柏木在色彩上互补, 犹如层层青峦。诗意缠绵的瓷和冷静平阔的木形成对比, 整个作品体现出一种平和收敛又包容互斥的能量。
而这种冷静表达的背后, 支持我的作品完成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对和谐的表达, 虽然和谐的同时存在着矛盾与反对, 材料的反对, 色彩的反对, 但我还是试图在反对中寻找和谐, 寻找其可以共存的元素。
三
在《皮囊壶》《瓷书》系列作品中, 我非常拒绝生涩的表达“观念”的形式, 取而代之的是用接近手工艺的处理手法来创作作这些作品。在《瓷书》之后我又很长一段时间沉寂与思考:如果我的《瓷书》继续做下去, 文本是否可以继续往前发展, 或者瓷书的未来会不会变成只是有简单意义的抽象雕塑?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回到材料的本质来考虑。这种本质不仅仅是对材料本身特点的探寻, 也是对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探寻。
而所谓的文化意义应该是对生活、对文化、对社会的一种个人体悟。《自述》《以死印生》等系列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产生的, 一种来自个人化、观念化的“物” (“艺术思维之物”) 的面貌将日渐清晰。
与在《瓷书》系列中瓷与木结合所传达的是“和谐”不同, 从《自述》《以死印生》开始, 我重新思考了瓷与木的关系——泥土的可复印性——泥土的物理特性之一。复制是为了还原与记忆。出于偶然的生活体验, 我对老旧的木制家具产生兴趣, 使得我的关注点从历史文本中转移至寻常生活, 我想, 这恰恰是艺术的本源之地。
在《自述》如图四这件作品中, 我将老家具所有突出的边角, 用泥土包裹, 每块泥土都形成内方外圆的两个形态:内形是家具的结构与纹路, 外形是包裹的软体形态。随着泥土干燥、开裂、瓦解, 最后我将脱落下来的瓷泥坯置入高温窑炉将之瓷化。在展示时, 瓷片被工整的安置在展厅, 形成零件集合的场域。这些白色或黑色的瓷片, 看上去似乎是物体的皮屑, 又有建筑或者工业零件的错感, 同时又有很强的书写感。好像一篇生活、环境、亦或是本人“自述”的一种物化方式。
《自述》系列的开始使得我重新考虑我的两种创作材料:木与瓷。不同于《瓷书》中比较简单的将两个材料进行“加法”, 《自述》更多的是考虑“减法”, 木与瓷的联系更像是一种概念上与空间上的关联。
与此同时, 树木的新芽, 树皮的脱落, 再一次使我体会到了自然的生死合一。我重新思考:木的本来, 木与瓷再次结合的可能性。树皮剥离了树木, 剥离了时间、剥离了生命, 成为了时间与生命的碎片。《以死印生》系列如图五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产生的, 我认为我所做的就是将这些碎片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储存。
我将捡来的或大或小几十块树皮一层层地涂上瓷泥浆, 累似漆器里脱胎的手法, 只是我木头部分我做了保留。最后将之置入窑炉中高温烧制。此时, 泥浆化为瓷质而树皮则化为草木灰釉, 最终达到瓷 (泥浆) 与木 (树皮) 的完全合一。
在我看来, 树皮是树死亡的痕迹, 正如死皮是人类细胞死亡的证据, 记录树皮剥离的状态也是在记录这个生命曾经活着的记忆碎片。记录这样的死也是在回忆这样曾经的生。在创作《以死印生》这件作品, 与其说这是创作, 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对转瞬即逝的祭奠。也许, 更难能可贵的, 这是“我做为我”对外界事物的全新认知, 也是“我”重新发现“我的初心”的一种方式。
而此时对于陶瓷这种材料我有了和之前《皮囊壶》不一样的认识。最初的《皮囊壶》系列是对陶瓷材料最直接的反映, 陶瓷在制作过程中的偶发性与空间感是吸引我创作的最大动力。《瓷书》系列中体现的理性中的反作用力是体现和谐的材质之美的最大体现, 《自述》开始我慢慢体会陶瓷作为创作材料的的社会层面的意义, 第三阶段的《以死印生》是我对人与自然作为生命较深层面的理解。
四
自从2005年第一次接触陶瓷, 无论是自然偶发的启示还是历史文本的引导, 最终到艺术思维的体悟, 给我的最大影响的是这些思维过程给予丰富的感官, 心理体验。我个人认为文中的三个阶段即:自然之物, 历史文本之物, 艺术思维之物内在还是一个递进体悟的过程。但无论怎么样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经历, 而艺术思维的快乐给我感情、认知、生命所带来的微妙变化和碰撞是当下的, 我认为对陶瓷材料进行创作, 是一个越来越走向思维解放的过程, 也是一个在艺术挑战、人生态度上越来越勇敢的过程。
摘要:“质物”是物质的本源, “本心”是我创作的初心。本文主要围绕“物质”之本源, “我心”之初衷为话题展开自己十年陶瓷创作之路中对现代陶艺创作的理解。也希望通过对自我创作的梳理, 总结并归纳出自我创作的方法论, 以此继续探寻未来陶艺创作之路的可能性。
叶芝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 篇2
(一)前期诗歌创作包括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芦苇中的风》。这一时期影响他诗歌创作的因素如下:
(1)雪莱的诗作特别是《阿拉斯特》和父亲约翰叶芝的影响,促使他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并从雪莱和斯宾塞等人的诗歌中吸收表现手法。
(2)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融进个人对爱尔兰乡间生活和民族神话的探索和思考,从中获取题材。
(3)唯美派诗人,特别是他同乡王尔德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主要是音韵、字句的雕琢技巧,但他对这些技巧的局限性也作出了透彻的认识。
(4)布莱克的神秘主义,叶芝用四年时间编辑创作布莱克的作品,这四年的研究丰富了叶芝的思想,培养他诗歌创作中运用想象的能力,逐步建立起一套神秘的象征主义。
(5)爱尔兰民主主义情节的影响,他试图通过写作创建出一种民族思想,从而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爱情诗中融入民族主义是他诗歌较鲜明的特征之一。
前期叶芝有代表性的爱情诗有《度人致所爱》、《叶落》、《蜉蝣》、《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尘世的玫瑰》、《爱的叹惋》、《当你老了》、《白鸟》、《两棵树》、《恋人述说他心中的玫瑰》、《鱼》、《恋人伤悼》、《他记起遗忘了的美》、《他赠给爱人一些诗句》、《他记起遗忘了的美》、《他赠给爱人一些诗句》、《他愿所爱已死》、《他翼求天国的锦缎》。
(二)叶芝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以及艾兹拉庞德的影响,诗风有了变化,他摆脱了唯美主义的倾向,用象征手法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在诗集《在七座森林里》(1903)和《绿盔》(1910)中,叶芝逐渐摆脱了凯尔特和神秘主义的一些影响。在1914年问世的诗集《责任》中,他早期抒情诗中超俗、迷幻的气氛消失了、表现出的是日趋成熟的精炼和坦诚,这以后叶芝的象征主义体系才日趋完善。1917年发表的诗集《库尔德野天鹅》使叶芝登上创造的顶峰。
这一时期叶芝有代表性的爱情诗有《箭》、《听人安慰的愚蠢》、《切勿把心全交出》、《亚当所爱的诅咒》、《呵,别爱得太久》、《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和解》、《面具》等。
(三)1919年到30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他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同时他创造性的把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情感融为一体。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对现实的思考。他完成诗歌创造的嬗变,体现出个人风格。他诗歌的成熟“既是个人风格的发展,也是技巧的提高”[2]
浅谈通感在诗歌创作构思阶段的运用 篇3
在诗歌创作的构思阶段,通感作为诗歌结构的发展环节,虽不多见,但于结构构思中一经使用,马上使诗歌结构灵蕴生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很多人最早接触通感这种描写手法是在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时,“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其实古代诗文中很多都使用了这种描写手法,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鸟抛软语丸丸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的彼此相通的描写,往往能把很抽象的事物描绘的更丰富可感。
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其著名论文《通感》中,从现代心理学、语言学里将“通感”这一术语引入文艺学,用来指称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独特的描写手法。随着通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认识到通感不仅仅是一种描写手法,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本文仅探讨通感在创作构思阶段的运用。
创作构思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极富创造力的一系列艺术思维活动,是文学创作的中心环节。作家在创作动机的催动下,急于释放胸中积蓄已久的心理能量,将奔腾于内心的无形的情感体验借助适当的感性形式表现、抒发出来。这时,作家就进入了艰苦的构思阶段。
在构思阶段,通感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构思方式。它在进行小说、戏剧等体制宏大的作品的整体构思时显得无能为力,表现出很大局限性,但却在短小诗歌的整体构思中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整体构思即创作主体在总体上所进行的把握与思考,它包括文学作品的主题确立、情节提炼、结构安排等一系列环节。结构,简言之,就是诗歌的内部构造,是诗歌构思的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结构把美妙新颖的立意、精细的感觉、饱满的情绪、奇妙的想象有机地组织起来,一首诗才能站立起来。结构象一座骨架支撑着全诗,又象一座桥梁连结着诗人的心灵与诗作。
那么得体、新颖的结构从何而来?这与诗人选取的结构的发展环节密切相关。常见的结构发展环节有: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展开、情感的贯通、角度的转换和对立物的并列等。将通感作为诗歌结构的发展环节,虽不多见,但于构思结构中一经使用,马上使诗歌结构灵蕴生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来看两首古诗:
咏 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咏柳诗,歌咏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在构思过程中,诗人先写他远远望见一棵颜色青翠的柳树,如玉石一般温润翠嫩,走近一看,细密的柳枝像千万条绿色的丝带一般柔软、翠绿。从柳树的整体形态到柳条的数量、颜色、情态,根据安排材料的一般顺序,接下来该写柳叶了。如按一般结构平实地描写下来,则此诗平淡无华,落于俗套。但此诗于结构构思时运用了通感,将通感作为诗歌结构发展的环节,使它在结构安排上胜人一筹,成为千古佳作。
诗人于春风中观赏柳叶,柳叶细长,整齐划一地随风摆动,像是专门裁剪过的似的。由春风与柳叶的相伴出现,诗人借助联想,将无形的春风比做视觉可见的明利的剪刀,它轻柔地嚓嚓响着,裁出了这无数片的细叶,这由触觉到视觉的感官挪移,使春风、剪刀、柳叶刹那间有机联系贯通起来。诗人将此通感抓住,并把它做为诗歌结构发展的环节,以一句设问“不知细叶谁裁出?”自然巧妙地转入对柳叶的描写,使平实的结构陡然灵动了起来。
塞上听吹笛
高适
雪净胡天牧马还,
月明羌笛戌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
风吹一夜满关山。
雪野茫茫,无边无际,似乎把塞外的天也映照得格外洁净明朗。在这一片雄美苍凉中,戍边的将士牧马归来,在明月朗照的戍楼里吹奏羌笛。他所奏何曲?前两句中并未写明,但从后两句来看,其所奏之曲应为《梅花落》。此曲为塞外胡人抒发思乡情感所作,用羌笛吹奏,音声哀婉惆怅,如泣如诉,令人有断肠之感。在结构构思过程中,诗人由《梅花落》的曲名联想到片片梅花随风飘落的情景,而《梅花落》曲抒发的思乡之情随苍凉的羌笛声传播到塞外的每一个角落,刺痛着每一个戍边人的心,就好像点点梅花在塞外劲风的吹送下,一夜之间撒满整个边关。这种以《梅花落》的曲名为诱因,将无形的笛声想象为视觉可见的梅花的现象即为通感。诗人将此通感作为诗歌结构的发展环节,后两句不再缀写笛声,而以“借问梅花何处落?”一句将笔触从听觉空间移入视觉空间,以梅花飘落,一夜之间溢满关山的视觉形象,表达戍边人的思乡之情。
这就是通感的魅力。它能够使事物之间特殊的内在联系沟通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怦然心动。
[1]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97.
创作阶段 篇4
1、早期: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试笔小说
劳伦斯初期的《白孔雀》、《逾矩的罪人》和《儿子与情人》 是悲剧性的小说。
劳伦斯体弱多病,但聪颖腼腆,善解人意,母亲对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爱。劳伦斯上中学时认识了杰西 • 钱伯斯, 与她建立了深厚友谊。杰西是个有思想、有见识的女性,她对劳伦斯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劳伦斯发表了处女作《下午的安静校园》,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早期作品中可看到他对母亲形象的赞叹和颂扬。
1.1第一部小说《 白孔雀 》(The White Peacock,1911):思想的探索
劳伦斯是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创作小说的,其作品带有现实主义成分。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开始试写长篇小说,是其思想的探索,是对潜意识自我的探索, 对奇怪、复杂的感情世界的探索。1911年劳伦斯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出版,在大学就读时,劳伦斯与小他两岁的高中同学杰西 • 钱伯斯维持恋情,性格柔顺的杰西成为爱米丽的原型。
《自孔雀》的现实意义在于她深刻地暴露了劳伦斯自己的困惑:处在自然与文明的激烈冲突和对抗之中,即将成热的男女们究竟该作何选择?另外,《白孔雀》作为劳伦斯艺术追求的奠基作,也为其人物形象成热的变化发展作了铺垫。
《白孔雀》始终龙罩看阴郁气氛,使其人物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本所在。《白孔雀》摆脱不了维多利亚时尚的束缚, 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
劳伦斯短短45年中(1885-1930) 沉疴缠身, 始终未能找到理想的境界。唯一寄托是把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以及父母的错误婚姻带来的心灵创伤,全都溶入了他精神追求的“生活”——小说之中了。《白孔雀》记录了青年劳伦斯开始自我剖析的心灵历程。
1.2 《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 1912):取材于女友海伦 • 科克的真实经历,表现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于冲突的主题。
第二部长篇小说《逾矩的罪人》标题“逾矩的罪人”体现了作家态度:西格蒙德由于逾越了传统的道德规范而成为 “罪人”,他的自杀罪有应得,是他为自己的行为而付出的代价。
西格蒙德逾越了传统道德规范,成为“罪人”而自杀。 西格蒙德的悲剧,是劳伦斯对英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抗议和质疑,是他对现代人荒诞的人生和命运的一种彻悟。
1.3 《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揭示主人公心理发展过程的现代主义小说
劳伦斯写作并修改以前的手稿,1910年10月开始写作, 1913年达克华斯出版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此书描写青年保罗无法挣脱具有强烈控制欲的母亲的保护,无法与青梅竹马的玛丽安以及女权主义者克拉拉发展正常的恋爱关系。玛丽安即是以杰西 • 钱伯斯为原型,而克拉拉身上则有着爱丽丝 • 黛克丝的影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恋母情结”在《儿子与情人》里得到了文学诠释。小说出版获得评论界好评,并不畅销。
2、中期: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独具一格的现代主义倾向
2.1 《虹》(The Rainbow, 1915)
1915年长篇小说《虹》麦修恩出版。描写厄秀拉企图冲破家庭和环境,走向外面的世界。《虹》没有任何大胆的性描写,但当时女权运动已经崛起,《虹》所宣扬的妇女解放思想无疑令当局大感震怒,最后被指控为禁书。
劳伦斯《虹》艺术地再现了三代夫妻间的心路历程。在主题上《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家继续了他在《儿子与情人》中对大工业生产严重侵蚀英国乡村的批判;另一方面,劳伦斯又开了英国文学先河-- 注重探索人的性心理, 通过一家三代人的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性关系的交往,以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性关系的可能性。
2.2 《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1920)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续篇。1920美国塞尔泽出版, 1921英国塞克版。小说描写了伯金和厄秀拉、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两对情人之间生生死死的恋爱关系。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作者对社会、对世人的失望。他的主人公成了他的代言人。
没有曲折的情节,意象串连起故事。生与死的意象贯穿全书。厄秀拉看的明媚皎洁的月光、清新怡人的树林,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爱情关系伴随着一连串象征死亡的意象。作家借用这些意象暗示死亡与新生。
3、后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
1926年10月劳伦斯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稿, 1926年2月至1927年第二稿,1927年11月至1928第三稿, 由佛罗伦萨出私人版。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代表作,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富争议小说之一。自问世后,因其中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而被视为色情作品,遭到广泛而严厉地批评将它列为禁书。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实际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是劳伦斯哲学思想、性爱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地展示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展示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生命原欲、自然本能的冲突抗争。
与死亡相对立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小说中与克利福相对立的人物是梅勒斯,他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总之,劳伦斯是处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这是一个以现代文明和工业扩张为标志的时代。劳伦斯又是一个有目的的作家,他的目的是做这个时代的反对者。 在小说中,作家将园林看守人梅勒斯描写成他自己的代言人,一个劳伦斯式的英雄。
摘要:研究劳伦斯小说创作的阶段,探索其文学历程,分析其现代主义创作特色。